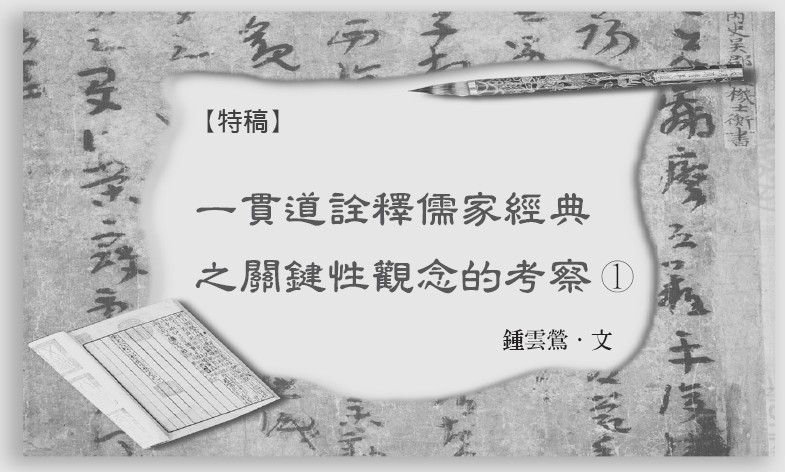
一貫道銓釋儒家經典之
關鍵性觀念的考察 1
摘要
本文的論述重心在於釐清一貫道詮釋儒家經典時所使用的關鍵性觀念與宗教語詞,我們可以發現,一貫道對於儒家經典的詮釋有其關鍵性的觀念,若不清楚這些觀念,可能會認為他們誤解了儒家思想。然而因為他們以宗教修持的理念詮釋儒家經典,使得儒家經典在民間社會得以廣傳,並且以宗教性的對話,開闢了儒家經典的另一注疏視野。
「理、氣、象」是一貫道教義的思想核心,其本體論與心性論乃在此核心思想中發展而來,並藉以區別神聖空間與一般空間、心之善惡與人性之源。
「道」與「教」之別是一貫道傳道所要宣揚的重點之一,說明「道」得之不易,是唯一的真理,可以讓修持者回歸本體,而「教」只具有教化作用,卻無法教導人回溯性命本源,故而認清「道」、「教」之別,成了一貫道詮釋經典時的重要觀念。
由於一貫道強調性、理之源,故而落之於人身之中,亦強調個人形體生命之源,配合河圖之相位,說明人之性命本源乃在「玄關」,而「玄關」位居人首之中,又位居河圖「五十中位」,故又稱「十字架」。「玄關」之說乃配合性理之論以說明人的性命本體,修道必須依此而修方能成道,故而一貫道對儒家經典的詮釋十分重視,對「玄關」的描繪,藉以說明千經萬典的核心,無非藉文字指明「玄關」本性的重要。
道統、心法與三期末劫是一貫道紹承明清以來民間教派的傳統,所不同者,一貫道強調現今「白陽期」是大道廣開普渡之時,故而人人可求聖人仙佛之道,更重要的,一貫道認為他們是孔門心法的正統,並以道、劫並降說明其救世渡人的緊迫性與合理性。
最後談到一貫道對「一貫道」的詮釋。以「理」為核心思想是一貫道教義的基礎,故而一貫道對宇宙本體、個體本源的解釋都離不開「理」。是以其亦將「一貫道」三字放置於「理」的範圍中,故而將「一」神聖化,認為「一」即理、即道。故而所謂「一貫之道」即將貫徹古今時空的本體,就個人而言,則是「得一」洞察生命本然的大人。
我們觀察一貫道詮釋儒家經典幾個重要性的觀念,可以發現,他們乃在「性即理」的傳統中將儒家經典宗教化,而且以「理」本體為核心,關於對宇宙本體、人之本性的詮釋,都離不開這個範疇,因此談「理、氣、象」、「道與教」、「玄關與十字架」、「道統、心法、三期末劫」、「一貫之道」,雖用不同的語彙,但仍環繞在「理」的思想核心,一切解釋,無非要我們對洞察本心本性的根源,進而回歸理天本體。
一貫道雖以宗教修持的角度詮釋儒家經典,卻也開創了儒家經典詮釋在民間社會的另一面貌,也使我們更能體認儒家思想對各個層面的影響,以及不同的發展,並且以不同的角度審思儒家經典在民間社會的演變與轉化。
關鍵詞:一貫道、理、氣、象、玄關、十字架、三期末劫
一、前言
儒家經典在民間社會中被賦予宗教意義,並且被視為宗教聖典,這是不爭的事實。從傳統知識分子所熟悉的儒家思想轉化成為宗教教義,在這個過程中,理學思想被神學化應是最關鍵之處。宋明理學對於儒家經典的詮釋,尤其在本體論與心性論上,為儒家思想體系注入新血,而這股新血面對當時與釋、道二教的論辯、交流,成為民間教派之宗教家轉化儒家經典成為宗教聖典的主因。(註1)
儒家經典被宗教化,早已有之(註2),姑且不論當時詮釋者的用意,儒家經典在傳承的過程中之所以亙古常新,最主要在於透過經典作者與詮釋者之間的不斷地對話(註3),使得儒家經典具有時代意義,從經典所涵蘊的生命,這些詮釋者不同的解釋角度,正是賦予儒家經典的新生命,而民間教派對儒家經典的詮釋著作,也可說是宗教家與儒家經典對話的成果。
一貫道是典型將儒家經典宗教化的宗教團體,從其十五代祖師王覺一(1830?∼1884?)開始,確立了以儒為尊的修行方向(鍾雲鶯,1995) 。根據王氏的著作:《大學解》、《中庸解》、《三易探原》、《一貫探原》、《理性釋疑》(清光緒二十一年由竹坡居士合編而稱《理數合解》),時而可見王覺一將理學思想轉化成為宗教語言,藉以建立該教派的「終極本體」與教義思想,而今日之一貫道所遵奉之修行理念與所信奉之教義思想,基本上是紹承王覺一的宗教思想。
今日研究一貫道者頗眾,然而多數多以「一貫道沒有自己的經典」做為批評一貫道的主因,認為一貫道沒有屬於獨立宗教的教義思想與經典。就筆者長期觀察民間教派詮釋儒家經典的作品看來,這樣的說法恐怕有待商榷,因為他們忽略了一貫道乃以儒家之理念做為修持目標的宗教團體,因此儒家的《四書》就是一貫道的宗教經典,是以一貫道對《四書》再詮釋的作品不勝枚舉,尤其是《大學》與《中庸》;再者,這樣的說法恐怕漠視了理學思想對民間社會的影響與理學思想被宗教化的事實,許多民間教派對儒家經典(尤其是《四書》與《易經》)之宗教式註解的著作,都說明了庶民社會對於儒家經典的了解,乃是透過這些宗教性的詮釋作品。因此,若以有無自己教派的經典來看儒家性的教派,這樣的角度恐怕有失真實。
黃俊傑教授曾說,中國的詮釋學是以「認知活動」為手段,而以「實踐活動」為目的。而「實踐活動」才是詮釋的本質,故又兼攝內外二義:(一)作為「內在領域」(inner realm)的「實踐活動」,意謂經典解釋者在企慕聖賢優入聖域的過程中,個人困勉掙扎的修為工夫。經典解釋者常常在註釋事業中透露他個人的精神體驗,於是經典注疏就成為並落實到個人身心上的一種「為己之學」。(二)作為「外在領域」(outer realm)的「實踐活動」,則是指經典解釋者努力將他們精神思想的體驗或信念,落實於外在的文化世界或政治世界之中(黃俊傑,1997:481-482)。本文嘗試從這樣的角度看待一貫道對儒家經典的詮釋,檢視民間教派對儒家經典的詮釋,特別是幾個重要的關鍵性的觀念,透過一貫道教內作品的研探,我們才能具體了解一貫道詮釋儒家經典的重心,也才能更清楚其教義思想與修道理念。
【註譯】
(註1)在許多儒家性的民間教派中,儒生居於重要的地位,尤其是落榜的儒生。根據梁其姿的研究,明末清中後期(1600∼1850)許多慈善機構反應出「儒生化」的現象,其中所蘊涵的意識形態,不單只是一些正統的儒家思想,而且滲入了不少一般百姓所能接受的通俗信仰。尤其乾隆以降,儒家的價值觀念更是被明顯的呈現出來。這些中下階層的儒生,處於士紳與百姓之間,其影響實不容小覷。梁氏的研究成果說明了當時百姓的價值觀念實取自於這群地位不高的「儒生」,可知這些落榜的「儒生」對庶民社會的影響。見梁其姿,《施善與教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1998年3月),頁4。又李孝悌先生的研究更是指出,十八世紀因人口數量的遽增,經濟的發展與受教育的機會增加,使得考試的競爭更激烈,不第或不得任官的現實,加深了被排除在官僚體系之外的挫折感,這種強烈的挫折感,致使士人從宗教的力量中找尋慰藉,李孝悌,〈從中國傳統士庶文化的關係看二十世紀的新動向〉(《中研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十九期,民國七十九年六月),頁307。而這些落榜的讀書人因與庶民社會最有直接的接觸,故受到民間宗教信仰的影響要大於中舉的士人,明代三一教主林兆恩便是典型的例子。
(註2)早在漢代,今文學家即藉讖緯之學將孔子神格化,許多緯書的災異符命之言皆偽託孔子之言,孔子儼然成為預言的神祇,不過,今文學家欲將孔子樹立成為教主的做法並沒有成功,參馮友蘭〈緯書中的世界圖式〉,《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三冊》(臺北:籃燈文化事業,民國八十年十二月)、金春鋒〈讖緯與宗教〉,《漢代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12月)。清末民初,康有為創立孔教會,仿照西方基督宗教的形式組織,奉孔子為教主,以孔子所作六經為聖經,以儒家的忠孝仁恕為教條,以尊孔之典為宗教儀式,全國遍設孔廟,令士庶男女膜拜祭祀。康氏的主張,隨著1917年7月張勳復辟的失敗,孔教運動也宣告失敗。參房德鄰〈從聖學會到孔教會〉,《儒學的危機與嬗變----康有為與近代儒學》(臺北:文津出版社,民國八十一年)。
(註3)3參黃俊傑〈從儒家經典詮釋史觀點論解經者的「歷史性」及其相關問題〉,《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一)通論篇》,(臺北:喜馬拉雅基金會,1992年6月)。
(作者簡介)
鍾雲鶯:基礎忠恕道場桃園區道親,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現任龍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