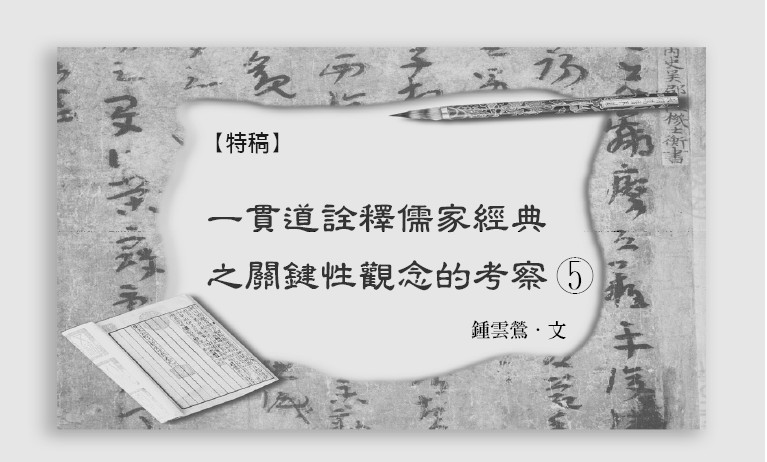
【特稿】
一貫道詮釋儒家經典
之關鍵性觀念的考察(5)
鍾雲鶯.文
(接上期)
雖然,「玄關」就在吾人身中,但若無明師指點,則苦修不知其所,因此一貫道特別強調「點玄關」求道過程的神聖性即在此。若能明白自性所在之處,則可體悟聖人仙佛所傳之千經萬典的宗旨目標,經典所言,不過是藉由文字傳達本體之奧妙,《學庸簡解》解釋《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
道出自理天,賦於人身謂之性,那麼道性一者一體也。今天我們得一,才知一之道理也,性得之理天,神為元神,隨身之有無,從受胎以得其生,凝於無極之中央(玄關),主宰生身之造化,故性在人存,性去人亡。所以人之軀殼不能離開這道也,離開即亡矣。(註19)
《學庸小註》解釋《大學》「在止於至善」時也說:
修道率性成真,達到理天最好的地方,即極樂世界。渡化世人達到最好的境界,叫人在生時,自性放在玄關處。(註20)
玄關乃主宰我們性命之所,故不可須臾離也,也可說是「道」降於人身之處,攸關性命之存亡。修道所要修煉者即在此處,歸根復命亦在此,達本還源也在此。而一貫道認為,儒家經典對「玄關」處的描述,乃將重點放置於《大學》的「明德」、「止於至善」以及《中庸》之「中」,(註21)《文外求玄---學庸註解》解釋「中庸」之意義時說:
「中」字之義,乃口中一直,上通天外之天,下貫大地九幽。
「口」字範圍上下左右霾方,即表示宇宙之意。「|」一直者,即無極之真理,太極之一?,至中至正,不偏不倚,法一之中道也。中道者,居於中央戊己之真中,真空生妙有,真虛統至實,由無形而生天地萬物之有形,由無聲而發天下萬種之有聲,萬靈萬彙之所從始,霾端萬善之所由生,即天之理、無極之真,是謂真天大道之奧竅,吾儒所謂「至善地」。(註22)
以整體而言,「中」乃宇宙之本,即是理天。就個體而論,本然之性源自無極理天,落入於個體之中,即是人的玄關,此處統領四端萬善,真空妙有,靈明至實,雖有而不知其有,卻是性命之大源,也就是《大學》所說的「至善」。《大學中庸講義》對「止於至善」之描述曰:
止於至善者,止於至在而不遷也。……止住在一竅,無聲無臭中至善之體也。……至善而明德也,止於至善者明明德也。孟子曰:十二時中,念念不離。有子曰:君子而時中。子思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矣。金剛經云:如是我聞,一時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五祖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道祖曰:返樸歸真。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清靜經云: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心經云: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在者止也)……惠能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註23)
所謂「止於至善」,在一貫道的解讀中,乃「止住一竅」,此一竅乃明德自性之本來面貌。以是引用許多聖人仙佛之言,以證三教聖人所言乃同屬一事。我們姑且不論其所用引文是否正確屬實,(註24)但是可以肯定的,他們所要表達的,都是對於自性的形容。儒取「中」之義以及《中庸》末章對至德之形容;道家則以「觀徼」與「真常之性」;佛家則以金剛經之無住之心與心經之般若及六祖惠能所說自性之本來面目,所強調者,皆要說明與生具足的光明自性。其中所引用的三教之言,皆是平民百姓較易接觸的經典與語詞,以此告知信眾三教聖人所言實是一事,修道必須得其「竅」,此「竅」即儒之「至善」,道之「玄牝」,佛之「金剛」,總而言之,都是對「玄關」的形容。因此一貫道詮釋《大學》時,只要談到「止於至善」,幾乎都會有「玄關」的字眼出現:
要止於至善定要明理,才不會半途而廢。要明理,一定要接受明師指點。
(註25)求明師指開玄關,即為知止地。(註26)
修道一定要「止於至善」才知為什麼要修道,才知修道本是自然,而非強人
所難。一旦知道這個道理,不論過程多麼艱辛,都會以修到「至善」之境為目標。而要知「至善」地,一定要經過明師指點,指出人人之自性處,指出明德本性所居之「至善地」。
【註釋】
(註19)謝金柱,《學庸簡解》(臺北縣板橋:正一善書出版社,民國八十七年), 頁95。
(註20)夢湖,《學庸小註》(嘉義縣:玉珍書局出版社,民國八十一年四月八版),頁10。這本書乃成書於民國六十八年。
(註21)這樣的解讀面向,基本上依循理學家的傳統,宋明以來,皆以先天內具純然的德性解釋「明德」。如朱熹解釋「明德」說:「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王陽明則說:「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對於「至善」的解釋,朱熹註解為「事理當然之極也。」王陽明對於至善的境界則說:「明德、親民之即則也。」,陽明認為「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然至善,其零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現,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也。」又說:「至善者,心之本體也。」這樣的解釋,對於明清以來民間教派對自我本體解釋的影響甚巨。
(註22)樵山老人著、林立人整編,《文外求玄----學庸註解》(臺北縣板橋:正一善書出版社,民國八十六年一月),頁102。本書成書於民國四十九年。
(註23)《大學中庸講義》乃早期一貫道道場之上課教材,作者、出版時間、出版者不詳。
(註24)一貫道對於經典的解讀,通常有「萬經皆我註腳」的傾向,他們以宇宙主宰與自我天命之性為讀經的重點,因此在經文的引用上,有時會有「斷章取義」或錯引,以及借經文之文字,做為解讀教義所用的現象。我們不能就此而責怪他們,因為他們對信仰有其宗教式的詮釋角度;再者,宗教的修行重視體驗與實踐,語言文字只是工具而不是修行的憑藉,這是宗教家與思想家面對經典詮釋的不同態度。
(註25)《學庸小註》,頁11。
(註26)《學庸簡解》,頁9。(續下期)